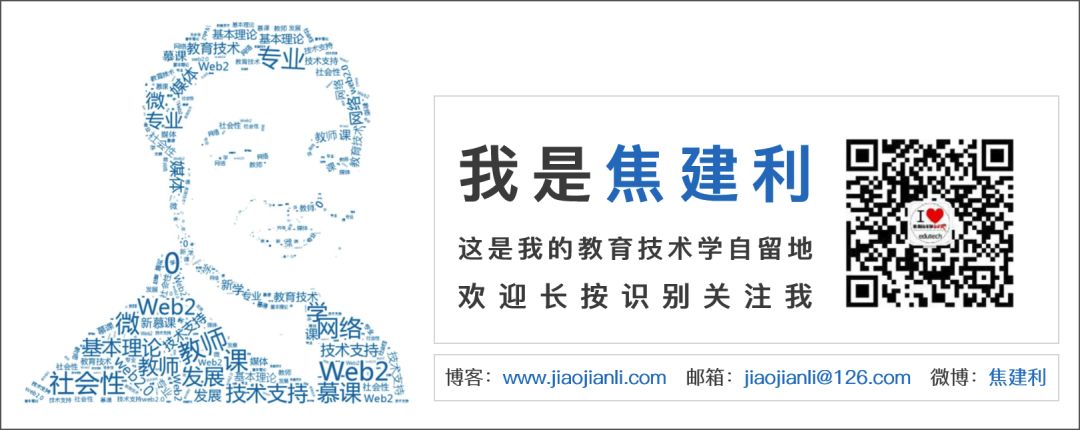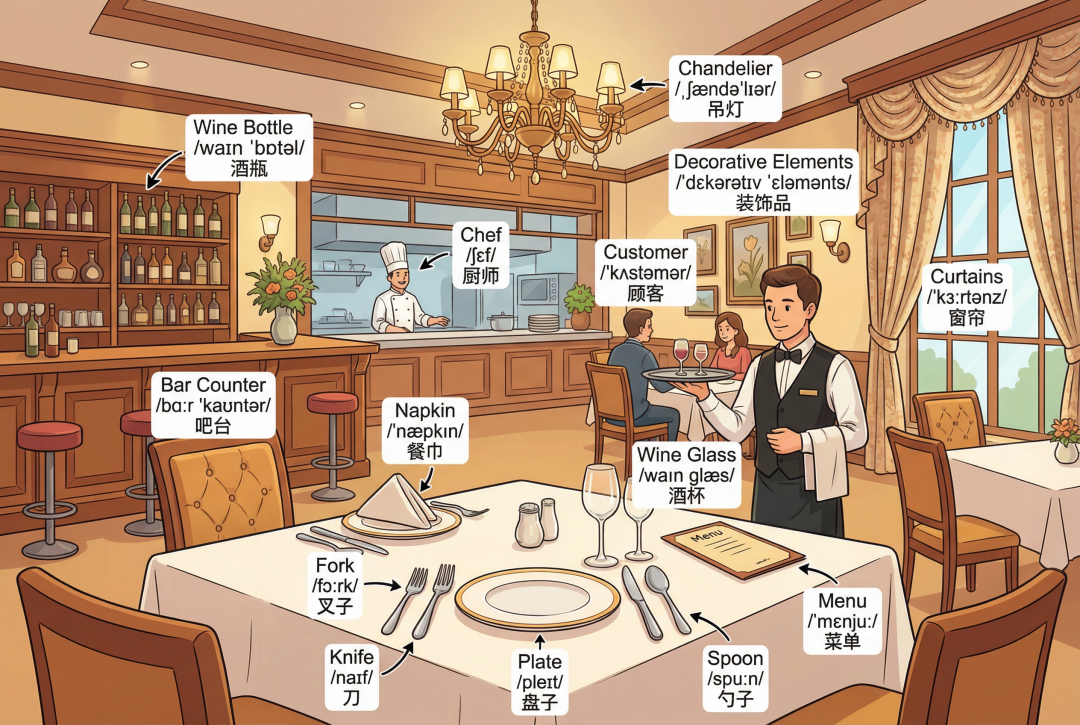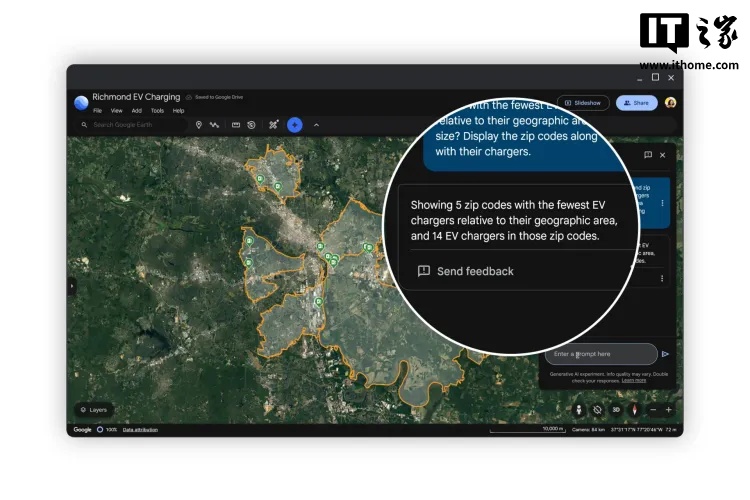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1987)提出著名的“索洛悖论”,“计算机无处不在,除了在生产率上找不到它的影子”(”You can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where bu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计算机的发明本应是一场带来生产率和生活剧烈变化的技术革命。“索洛悖论”揭示了当时信息技术革命中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在信息通信技术蓬勃发展并快速普及时,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却未出现与之相称的跃升。20世纪90年代,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及其同事也提出了“生产力悖论”——尽管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计算机在工作场所的普及,但生产力增长依然缓慢。该悖论表明,仅仅依靠新技术不足以推动生产力;组织变革、技能和业务流程创新等补充因素至关重要。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悖论可以被看作是“索洛悖论”在信息技术时代的一个延伸、回应和解释尝试。无论是“索洛悖论”与“埃里克·布林约尔松悖论”,似乎都在揭示了信息技术投资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显著不一致性。而今天,随着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快速发展,
AI技术是不是“索洛悖论”的一个新例?人工智能对学校教育是否也同样存在“生产率悖论”?自“索洛悖论”提出以来,围绕这一现象,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展开了广泛研究和讨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增长实验室”伍晓鹰主任指出,学术界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四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解释。第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解释是测量误差(mismeasurement),认为计算机技术进步并非没有带来生产率提升,而是尚未能够被现有统计系统在投入、产出、价格诸方面准确辨认,从而被纳入现有增长核算框架中。比如,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产出(如学生批判性思维、创造力)的难以量化性可能掩盖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真实影响。第二种看法是时间滞后(time lags),也就是计算机技术的生产率效果具有时滞性,不会反映在当期的经济指标之中。第三种解释是再分配效应(redistribution effect),强调计算机技术在催生新产业、新职业的同时,可能导致旧产业、旧职业的萎缩甚至消亡,当两者完全抵消时,就不会有生产率效果。第四种解释聚焦于制度和组织层面的“管理不当”(mismanagement),认为在制度尚未适应技术变革的情况下,其潜在价值可能因资源错配、激励失衡或治理滞后而难以释放。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5993531560/1653e08a802001i3uo
在教育领域,这一悖论表现为尽管教育技术持续革新,但教学效率、学生学习成果等核心指标并未呈现显著改善。这种现象,在教育科技的百年历史上似乎也屡见不鲜啊!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各阶段,技术应用对教学效率的量化影响均低于预期。比如,不少研究报告,平均教学时长未显著减少;学生成绩提升幅度有限(非显著性差异现象变成明证);学习成果增长率未出现拐点式提升。所有这些,均表明,教育领域的生产率悖论持续存在,且随着技术演进呈现新形态。学者们对生产率悖论所提出的多种解释,似乎同样也适用于教育场景:1、测量问题:教育产出(如学生综合素质提升)难以准确量化;2、学习时滞:教育者需要时间适应新技术并优化教学流程;3、技术特性:教育技术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其影响需长期显现;4、组织适应:学校制度和教学文化变革缓慢。这些因素共同表明,教育科技的投资回报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和更精细的测量方法才能充分显现。当前,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正处于类似1990年代IT行业的“悖论期”,技术潜力巨大但宏观效益尚未充分显现。
如何正视、理性看待和科学破解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力悖论?这应该是摆在教育政策制定者、教育研究人员、以及管理者面前的一个时代课题。为此,我们需要采用更全面的价值测量框架,积极推动技术深度整合的教学重构,实施与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相配套的制度创新,保持战略耐心关注长期收益,坚守和维护教育的人文关怀。展望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开发AI教育生产率的多维评估工具;开展纵贯研究追踪AI教育影响的长期轨迹;深入分析组织制度因素对技术转化的调节作用。我们相信,只有通过技术、 教学法和制度的协同创新,才能最终实现人工智能教育所承诺的生产率提升,使教育真正进入智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