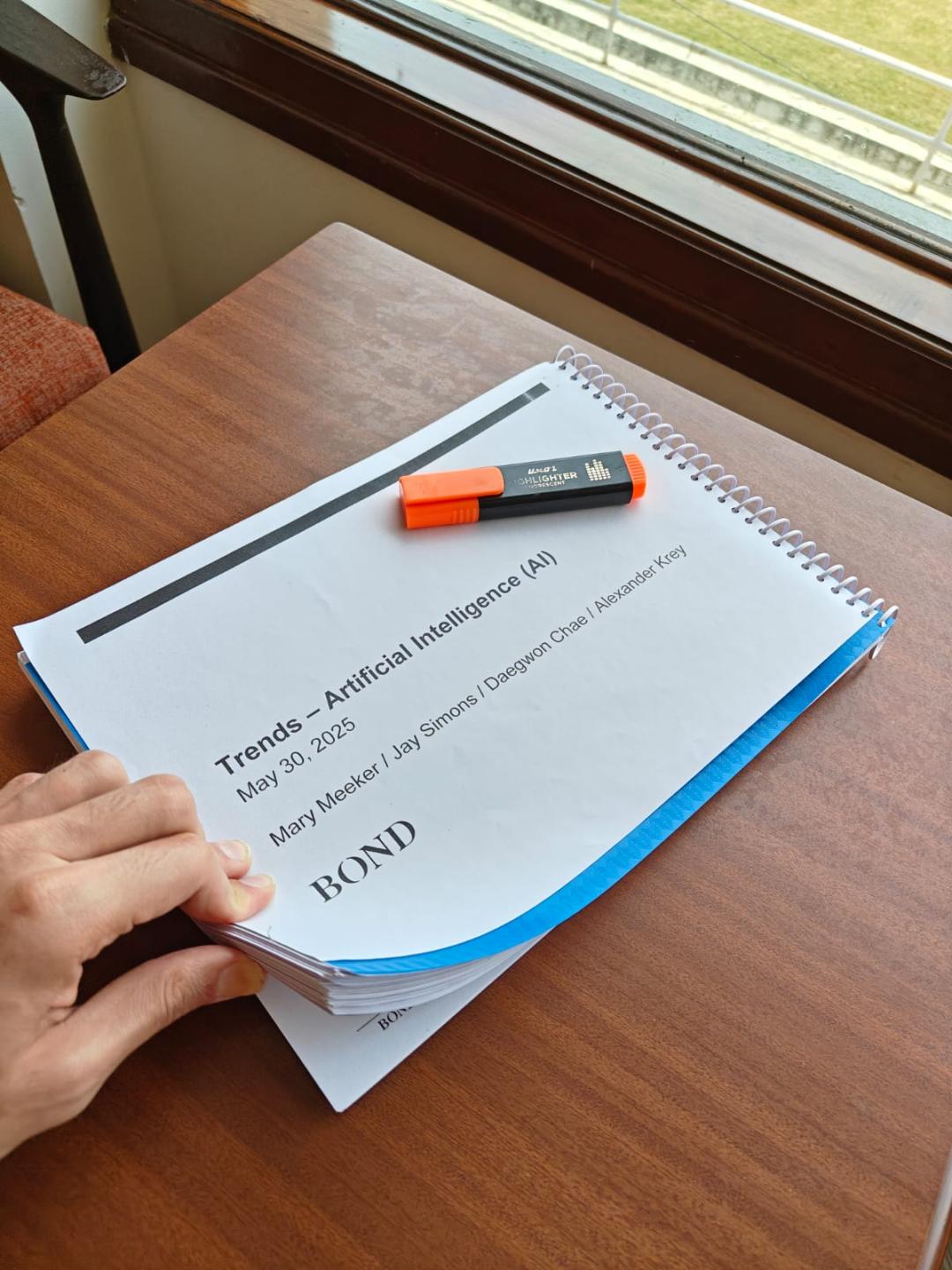大年初四,羊日大吉。祝愿您三阳开泰,好运连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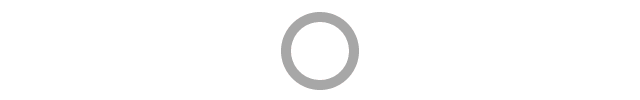
Jeppe Klitgaard Stricker是丹麦人,他是丹麦奥尔堡大学(Aalborg University)临床医学系行政主管。同时,通过www.stricker.ai网站,Jeppe 以作家、演说家和顾问的身份,从事高等教育领域生成式AI的研究与应用。

https://www.stricker.ai去年年底,在自己的自媒体上,Jeppe发表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对2026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自己的预测。在这篇题为《2026年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7个要点》(7 Points On Generative AI And Higher Education For 2026)的文章中,1. 我们正在失去提出不明确问题的能力Jeppe 的这个观点算是比较温和的。极端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正在丧失提问的能力。提问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提出一个“不明确”的问题,往往是人类好奇心和创造力的起点。而对于个体而言,提出一个不明确的问题,需要花费时间去梳理、试错和等待灵感。而人工智能则可以为我们提供即时满足。为此,在AI时代,守护那种敢于面对混沌、勇于提出看似不明确但富有启发性问题的能力,或许是人类保持独特创造力的最后堡垒。2. 如果我们不谨慎,人工智能素养就会沦为供应商培训。这个观点我相信在这个领域的人都应该会认同的。在过去几十年,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历程中,在许许多多的地方,教育信息化、数字校园、智慧教室……,有多少项目、工程、计划,差不多沦为了供应商跑马圈地的地方。教育信息化培训不难成为供应商的培训。人工智能素养也是如此,地方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学校管理者必须高度警惕,科学决策,慎之又慎啊!3. 高等教育中的大多数人工智能政策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很是认同Jeppe的这个断言,而且我认为,他的这种断言在国内许多大学也是成立的。为什么?因为许多高校出台AI政策可以说是滞后的,这种“消防队”式的政策往往是应对已经发生的危机(如学生大规模使用AI完成论文)而仓促出台的。这些政策的首要动机是风险管理和学术诚信,而非教学创新。许多高校的相关政策往往将监督和执行的压力完全抛给一线教师,却没有提供足够的培训、支持和时间。之所以说是“毫无疑义的”,是因为绝大多数都是缺乏执行力的。这并不是要否定高校进行人工智能规管与治理的必要性,而是在呼唤一种范式转移。
4. 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意味着我们也应该使用。学生使用某种工具(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能成为教师、学校或其他人也必须在教学场景中使用它的充分理由。教师的职责是引导学生正确使用工具,而不是被学生的行为牵着鼻子走。教育工作者需要根据教育目标、伦理规范和教学效果来决定是否使用AI,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学生的行为。技术的发展需要教育工作者做出更高层次的、更负责任的回应。5. 合成知识是有长期代价的——我们只是尚未看到而已。所谓合成知识(Synthetic Knowledge)是指由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通过分析海量数据后,重新组合、生成的内容。它看起来像知识,甚至符合语法、逻辑严谨,但它没有经过人类大脑的亲身验证、思考挣扎和情感体验。在人工智能时代,由AI生成的、看似正确但并非人类通过亲身学习、实践和思考得来的知识(即合成知识),虽然当下看起来很方便、很高效,但长远来看,它可能会对人类的能力、社会结构和文化认知造成深刻的、不可逆的负面影响,而这些负面影响目前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6. 所谓的“效率”往往仅仅是指速度。过去这几年,人们听到最多的,恐怕要数“减负、增效、提质”。这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进入教育领域时最诱人的承诺。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奔着“减负”去的,无论是学生,还是一线教师。“减负”没错,“追求效率”也没错。然而,教育是慢的艺术。人们抱着“减负”的初衷拥抱AI,却因为过度迷信“效率”而陷入了新的焦虑。真正的出路可能在于:用AI的技术理性去对抗那些繁琐、重复的“伪负担”,从而守护教育中那些必须“慢下来”才能发生的“真成长”。让技术去做技术的擅长的事,把人解放出来,去做只有人才能做好的事——那就是在漫长的时光里,静待花儿慢慢开放。7. 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建立的新关系和习惯可能会持续一生。当人们开始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如智能聊天机器人、虚拟伴侣等)建立情感联系,并养成依赖它们来满足某些需求(如陪伴、决策、信息获取)的习惯后,这种互动模式和情感纽带可能会变得非常牢固,甚至伴随他们一生。也就是说,我们与AI的互动,可能会像过去人们写信、后来人们刷手机一样,成为一种深刻且持久的生活习惯,最终重塑我们作为“人”的社交方式、情感模式和思维习惯。


Photo by Johnnie Walker